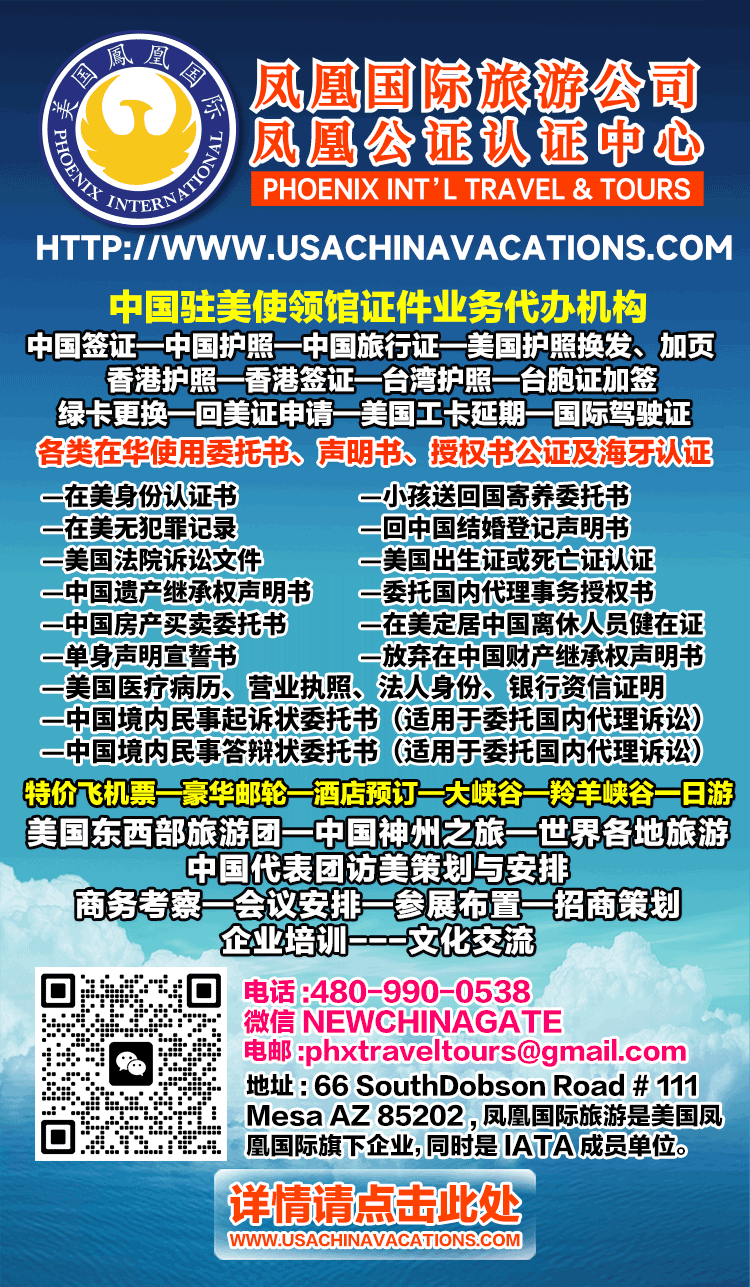李老师/汪兴旺
阅读量:2万+
调整文字大小:
汪兴旺
李老师是我读小学一年级时的班主任,她叫李忠玲,上海人,三十出头,瓜子脸,皮肤白皙,身材高挑,操着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,有一种城市知识女性的高雅气质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李老师举家由上海下放到安徽农村,落户于我临近的生产队,当过幼师的她被大队安排教民办。从繁华的都市来到贫瘠的乡村,李老师每天和学生娃在一起,一待就是十几年。
由于教室紧张,大队决定,腾出毛笔厂的库房做一年级临时教室。库房低矮、破旧,勉强放下十几张课桌。在这裡,李老师曾教过我一年级,所有课她一个人教。讲台上放着她从上海带来的闹钟,“滴滴滴”上课的闹铃一响,男同学赶紧从隔壁堆放的笔杆垛上滑下来,顾不得满头大汗,纷纷回到座位;女同学则揣着毽子熘回教室。我是班长,当李老师往讲台上一站,我就喊“起立——”,同学们齐刷刷地站起来,异口同声地说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。”见李老师微笑着点头,我脱口而出:“坐下——”
有一次,正喊“坐下”,忽听“趴”的一声,张五三同学一屁股跌在地上,原来他的那条歪凳子腿折了,他的裤子被跌破了,屁股处露出两个大窟窿眼,引起哄堂大笑。张五三家弟兄多,衣服老大穿小了老二穿,老二穿小了老三穿,轮到他身上差不多不成样子。李老师瞭解到他家境困难,拿出自己家孩子的新衣给他穿,还认他做乾儿子,张五三同学摇身一变成“上海佬”。李老师的乾儿子不止一个,李老师常常给他们带上海的玩具,让我们嫉妒得要命。
其实,李老师把所有的学生娃都当成她的孩子。有一回,李老师因有事让我们自习,事先告诉我,谁课堂打闹,就叫我记名。身为班长的我彷佛成了小老师。开始同学们都很自觉,后来就有个别同学交头接耳,做起了小动作,教室裡嗡嗡起来。我如实记下几个同学的名字,旁边的同学见状,担心我记了他的名字,从作业本上撕下两张没写的纸送给我。这一来,其他同学也跟着效彷,一张张白纸像雪片似的朝我飞来,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快意,叠好纸,哇,能装成一本厚厚的本子,这下不愁没纸写了!此时的我飘飘然,早已把李老师的话抛到“爪哇国”去了,把记上名字的纸条撕了。后来,也许李老师发现同学们的作业本都少了页,经查问,终于露出了马脚。李老师熊我:几张纸就能买到你,还当班长呢,这叫“受贿”!以后可不许这样噢!我羞得满脸通红。
不几天,李老师到我家家访,我有些不好意思,母亲特地炒了番瓜子,李老师直夸我字写得好,比赢了三年级的字,父亲很高兴,用手指了指压在罎子口的一叠纸说,他妈长年煎药,包草药的纸都给他写字了,一天写一张,压在坛口一大叠。李老师“哦”了一声,她似乎想起我挨批评的事。第二天,让我惊喜的是,李老师送给我两本本子,我认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。
星期天,李老师安排同学们到她家补课。李老师家住山坡上,屋前屋后,是成片的枞树林。做完作业,我们三三两两到坡上玩,山雀们在枝头雀跃,我们在林间嬉闹,好不开心!李老师像招待小客人一样招待我们,此时,在我们心裡,她是一位和善可亲的阿姨。李老师爱给我们讲故事,带我们玩游戏,她讲的童话故事绘声绘色,声情并茂,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。可惜一年时间太短,李老师不是跟班上,她又有了新的学生。
三年级那年,由于教师变动,李老师又代过我们一段时间课,师生重逢,分外亲切。课馀,李老师问我们听不听故事?同学们高兴地鼓掌欢迎。李老师捧着一本书边读边讲,故事的小主人翁,跟我们年龄相彷,但他从小给地主干活,受尽凌辱,为了寻找童年的快乐,有一天他和小伙伴偷偷跑到山上,采野果,捉蝈蝈,竟忘记了下山……我的思绪不知不觉融入故事情节中,与小主人翁同喜同悲。可是,李老师只讲完几个章节又调回去了,我们不捨得她离开。盼呀盼,再也不见李老师回来讲故事,而那个小主人翁的命运一直悬在我的心裡。我读完小学,李老师仍坚守在那间破旧的教室,默默教着一届又一届小同学。直至八十年代中期,李老师一家才陆续返城。
四十年过去了,想必李老师已成了白髮老人。她也许不知道,在遥远的乡村,曾经的学生仍惦记着她,还有那没讲完的故事。
李老师是我读小学一年级时的班主任,她叫李忠玲,上海人,三十出头,瓜子脸,皮肤白皙,身材高挑,操着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,有一种城市知识女性的高雅气质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李老师举家由上海下放到安徽农村,落户于我临近的生产队,当过幼师的她被大队安排教民办。从繁华的都市来到贫瘠的乡村,李老师每天和学生娃在一起,一待就是十几年。
由于教室紧张,大队决定,腾出毛笔厂的库房做一年级临时教室。库房低矮、破旧,勉强放下十几张课桌。在这裡,李老师曾教过我一年级,所有课她一个人教。讲台上放着她从上海带来的闹钟,“滴滴滴”上课的闹铃一响,男同学赶紧从隔壁堆放的笔杆垛上滑下来,顾不得满头大汗,纷纷回到座位;女同学则揣着毽子熘回教室。我是班长,当李老师往讲台上一站,我就喊“起立——”,同学们齐刷刷地站起来,异口同声地说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。”见李老师微笑着点头,我脱口而出:“坐下——”
有一次,正喊“坐下”,忽听“趴”的一声,张五三同学一屁股跌在地上,原来他的那条歪凳子腿折了,他的裤子被跌破了,屁股处露出两个大窟窿眼,引起哄堂大笑。张五三家弟兄多,衣服老大穿小了老二穿,老二穿小了老三穿,轮到他身上差不多不成样子。李老师瞭解到他家境困难,拿出自己家孩子的新衣给他穿,还认他做乾儿子,张五三同学摇身一变成“上海佬”。李老师的乾儿子不止一个,李老师常常给他们带上海的玩具,让我们嫉妒得要命。
其实,李老师把所有的学生娃都当成她的孩子。有一回,李老师因有事让我们自习,事先告诉我,谁课堂打闹,就叫我记名。身为班长的我彷佛成了小老师。开始同学们都很自觉,后来就有个别同学交头接耳,做起了小动作,教室裡嗡嗡起来。我如实记下几个同学的名字,旁边的同学见状,担心我记了他的名字,从作业本上撕下两张没写的纸送给我。这一来,其他同学也跟着效彷,一张张白纸像雪片似的朝我飞来,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快意,叠好纸,哇,能装成一本厚厚的本子,这下不愁没纸写了!此时的我飘飘然,早已把李老师的话抛到“爪哇国”去了,把记上名字的纸条撕了。后来,也许李老师发现同学们的作业本都少了页,经查问,终于露出了马脚。李老师熊我:几张纸就能买到你,还当班长呢,这叫“受贿”!以后可不许这样噢!我羞得满脸通红。
不几天,李老师到我家家访,我有些不好意思,母亲特地炒了番瓜子,李老师直夸我字写得好,比赢了三年级的字,父亲很高兴,用手指了指压在罎子口的一叠纸说,他妈长年煎药,包草药的纸都给他写字了,一天写一张,压在坛口一大叠。李老师“哦”了一声,她似乎想起我挨批评的事。第二天,让我惊喜的是,李老师送给我两本本子,我认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。
星期天,李老师安排同学们到她家补课。李老师家住山坡上,屋前屋后,是成片的枞树林。做完作业,我们三三两两到坡上玩,山雀们在枝头雀跃,我们在林间嬉闹,好不开心!李老师像招待小客人一样招待我们,此时,在我们心裡,她是一位和善可亲的阿姨。李老师爱给我们讲故事,带我们玩游戏,她讲的童话故事绘声绘色,声情并茂,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。可惜一年时间太短,李老师不是跟班上,她又有了新的学生。
三年级那年,由于教师变动,李老师又代过我们一段时间课,师生重逢,分外亲切。课馀,李老师问我们听不听故事?同学们高兴地鼓掌欢迎。李老师捧着一本书边读边讲,故事的小主人翁,跟我们年龄相彷,但他从小给地主干活,受尽凌辱,为了寻找童年的快乐,有一天他和小伙伴偷偷跑到山上,采野果,捉蝈蝈,竟忘记了下山……我的思绪不知不觉融入故事情节中,与小主人翁同喜同悲。可是,李老师只讲完几个章节又调回去了,我们不捨得她离开。盼呀盼,再也不见李老师回来讲故事,而那个小主人翁的命运一直悬在我的心裡。我读完小学,李老师仍坚守在那间破旧的教室,默默教着一届又一届小同学。直至八十年代中期,李老师一家才陆续返城。
四十年过去了,想必李老师已成了白髮老人。她也许不知道,在遥远的乡村,曾经的学生仍惦记着她,还有那没讲完的故事。
【凤凰华人资讯网报道】
分享到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