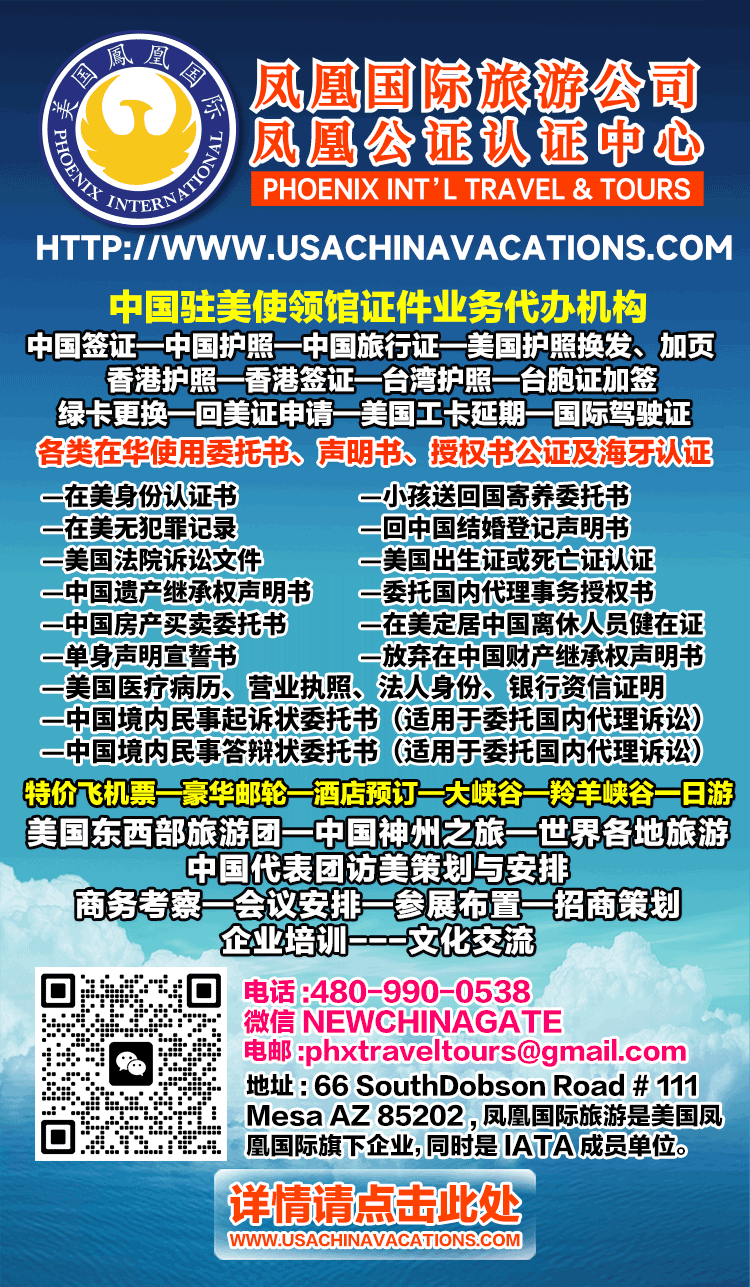回眸一笑 我的教育实践与思考(连载十一)
阅读量:1万+
调整文字大小:
作者:张鹤立

2015年8月,张鹤立女士在澳大利亚珀斯,为当地中文教育界人士介绍“鹤立教学法”与“鹤立教材”
下卷
十三、得陇望蜀
到1991年的9月,且不说是大是小,是好是坏, 我们在南阳已经有了四所幼儿园,在园的幼儿也达到四百多了。这里除了有前文述及的永安村幼儿园、唐河幼儿园、桐树庄幼儿园之外,还有后来创办的丝织厂后街幼儿园。
此时,唐河的幼儿园还是几十个孩子,只赔不赚;丝织厂后街幼儿园刚开办不久,也是只有投入没有回报;而桐树庄幼儿园则成为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,每个月大概能有二千元的利润,这对当时的我来讲,已经相当可观了。
尽管发展势头还好,幼儿园也基本进入良性运行的轨道,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南阳不是最佳选择,也不是我的久留之地。直觉告诉我:在南阳,难以大跨度地实现我的教育追求与梦想。
一是地方小、人口少,这就意味着市场有限、规模受阻、舞台太小,难以唱大“戏”。我那时有一种感觉:在南阳市的西边打一拳,就会把东边的人打倒,也就有这么大范围!就算在南阳各个区域,都发展起我们的幼儿园,从规模和数量上也难以达到我们的理想状态。
大家了解蛇和蚕吗?蛇和蚕长到一定程度,就要蜕皮。这时,它把身体从原来的壳中解脱出来。只有这样,它才能够继续长大;不然的话,那层已经板结的皮囊,就会抑制它的生长。虽然在蜕皮的过程中它显得很弱小很无助,甚至失去抵抗和防御的能力,成为天敌的美餐,但它必须这样做,否则它就没办法长大,没办法成熟,没办法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我意识到我也到了“蜕皮”的阶段。南阳的狭小,就好比是蛇和蚕的外皮,当我们“长”到今天的程度,已经感觉到了它的束缚和限制。只要我们想长大,就应该从这张“皮”中解脱出来。
不知为什么,鹤立教育总有一种“长大”的渴望,总是充满“长大”的激情。如果它一天不在品质和规模上有所提升和发展,就会觉得不大对头。一年多来,我们从一个孩子到几个孩子,从偏居西北的小门小户到市区有名有姓的幼儿园,从一所幼儿园再到现在的四所;一般的眼光来看,发展速度也算可以,可为什么还不满足,还不停下来舔舔伤口,梳梳羽毛,而要继续奔走,继续远航呢?没办法,我的体内一直鼓荡着“长大”的激情,充溢着发展的热望。这种激情和热望,虽然有时候让我盲目,让我失足,但我认为这是技术的问题,是思维方式的问题,而激情本身并没有错,它需要的是理性的控制和告诫,而不是消减和冰冻。
我相信,任何人的成长和发展,任何企业的成长和发展,包括一个团队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长和发展,其内在的动力都离不开这种激情和渴望。这是生命最本能的冲动,是生命上演的剧目之所以丰富多彩、波澜壮阔的最根本的原因。就好比整个生物世界从简单到复杂、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就离不开这种内驱力一样。
一个孩子最强烈的冲动就是长大,这是最本真的童心,而只有保留这种童心的人,才能不断地获得发展、求得进步。一个企业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若想发展、进步,又何尝不需要这种“长大”的冲动呢?我相信:如果什么时候失去了这种热望,那么未老先衰的征兆就会出现。
中国的企业和国外的企业相比较,从总体来看,其发展的速度、规模和层次是相距甚远的。我想,一个最重要的原因,就是我们普遍缺少这种“长大”的激情和渴望。我们奉行“小富即安”、“知足常乐”、“求安求稳”的信条;只关注物质生活,而缺少精神生活的需要,在“吃饭活着,活着吃饭”的层次上徘徊,而缺少社会责任感,缺少对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;所以够吃够花就行了,何况不仅够这一辈子吃喝,连下一辈都够了呢!
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,当一个人、一个企业、一个团队解决了生存问题,进入小康状态之后,发展之“火”就开始缺“氧”,也就失去了继续长大的冲动与激情,这应该是中国很多企业,包括幼儿园,出现“盆景效应”和“侏儒症”的原因吧。
我们为什么要长大?说到底这是生命应有的追求与冲动。你问蛇和蚕为什么要蜕皮?你问蝌蚪为什么变成青蛙?幼虫为什么变成蝴蝶?山上的树为什么从岩缝中倔强地生长并不断地指向蓝天,难道这需要理由吗?如果说理由的话,那就是这些生物体自身的使命。
鹤立教育要完成自己的使命!
谢天谢地,这种小农意识虽然不能说对我没有影响,但起码我还没有完全被它控制,这大概要感谢我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。从我父亲那里,我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种影响:作为人要活得有价值,要杰出、要创造、要有所作为,而不能虚度年华,愧对生命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化开始蜕变成了“侏儒文化”、“盆景文化”。而这种文化的典型特征,就是不许长大、不许卓越、不许杰出。而让你变得平庸得不能再平庸、渺小得不能再渺小,甚至让我们丢掉很多“人”的本质和特性,变成一头“猪”—一头只知道吃吃睡睡,摇头晃脑,至多再加上个传宗接代的“猪”,以防断了香火。
在我生活的青少年时代,接受的都是这种教育。为了摧残个性,毁灭创造,还发动了一系列破坏性极强的运动,什么反对“白专道路”,不许“成名成家”,甚至“读书无用”,做“白卷先生”,做四肢发达、大脑贫乏的劳动者。人们只能躺在物质生活的泥潭里打滚,而不能有精神生活、情感生活,不能有梦想,不能有境界和追求,更不能有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理解。
多么可怕!这不正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吗?这不正是我们文化中最黑暗、最不人道的一面吗?她让人不能作为人来活着,而只能作为物、作为畜牲来活着。
我有幸没有被这种文化彻底吞没。我怎么能不心怀感激、来响应生命对我的呼唤呢!所以,我必须长大,我要“蜕”去南阳这张“皮”,而给自己寻找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在南阳,存在着的第二个问题是交通不便。那时南阳没有主要铁路干线经过,距离郑州这个交通枢纽也比较遥远。当年乘坐汽车需要12个小时,而且路况很差。至于那时的车况就更糟了—破烂、狭窄,四处透风,哗啦啦地响;而车主为了多拉乘客,两排座位挤得人都喘不过气来,用来治“罗锅”正好。
汽车在这样的道路上行驶,不仅颠簸,而且还不安全。路两边的脏、乱、差也影响人的心情。如果不是万不得已,又有谁愿意品尝这样的滋味呢?
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鹤立教育难以向外传播,我们既不方便走出去,外边的人也不愿意走进来。而这不符合我的理想、我的意愿。
从我独立办学的那一天开始,我就盼望着能让鹤立教育走遍全国,走向世界。虽然当时还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和方式是什么,但我知道这一天肯定会到来。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向这一天逼近、靠拢,我下一步想采取的步骤也必须围绕这个目标。可是在南阳,这只能是遥远的梦想。
我在念大学的时候,学的是汉语言文学,但真正对我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是生物学和东方哲学。生物学让我体验到了生命的神奇与美妙、和谐与珍贵,连一只虫子,其生命都弥足珍贵,更何况我们人类!人类是宇宙的杰作,是上帝的珍品,是日精月华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形成的结晶。
作为个体,人的生命都来自于极端的偶然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战战兢兢地呵护她,不怀着虔敬的情感去打磨她。观照现实,我们会发现较长的一段时间里,生命在教育的视界里历来是缺席的。审视教育过程中对生命的浪费、作贱、扭曲的现象更是让人瞠目结舌,无法忍受。我在了解和感受生物发展的过程中,被塑造了,被提升了,使我产生了由此及彼的情感—从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角度,拓展到对其他生命,尤其是对年轻人的生命负责任的高度。我深知若实现这种愿望,我的脚步不能停留在南阳这个地域内。
说到这里,肯定有人说我狂妄、自负,但我可以坦然地告诉你: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,我就是将这项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使命。我感觉,有这种心态的人不是多了,而是少了,而我居然是这少数中的一位。对此,我感到骄傲,我感到自豪。
我认为南阳不理想,还有第三个理由:南阳属于中小城市,缺少号召力、影响力,不具有制高点上的战略价值,势必影响人们对鹤立教育的认可度以及积极追随的心态。
人们往往爱屋及乌,因为向往这座城市,便也不自觉地对这个城市的相关事物喜爱起来,靠自己的想象给它涂上金边、插上鲜花。相反,假如一座城市在人们的心目中评价不高,那么与它相关的事物,即使再好、再出色、再卓越,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也要打折扣。就像人出国旅游一样,到了国外即使东西再贵,再假冒伪劣,也要买上一大堆。回到家里才发现,家门口的商店里就有,比国外便宜得多,而且质量可靠、维修及时。但家门口的东西他偏偏不买,偏要到国外受骗,人有这种心理,你又如之奈何呢。
特别是我们中国市场开放时间不长,大家的市场经验还比较匮乏,缺少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能力。所以,就像小品《卖拐》中的范伟那样,容易被赵本山“忽悠”。人们愿意追星,愿意崇拜偶像,城市也有明星城市、偶像城市,而像北京、深圳、广州比起南阳来肯定要“明星”一些、“偶像”一些,甚至郑州比起南阳也不知道优越多少倍—尤其对河南境内的城市来讲。
因此,鹤立教育应该抢占战略制高点,这样才能对更广阔的空间形成辐射、产生影响。这既是在空间上的制高点,也是在人心理上的制高点,使大家乐于认同与追随,这便是我所说的战略意义。
前面谈到我对东方哲学的接触和热爱,我认同这种哲学思想中体现出的整体—联系和辩证—变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,而这也是我进行战略思考的哲学依据。
什么叫战略思考呢?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关注局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,相互制约,促成各要素之间的整合与互动。与此同时,再在关系中辨别孰轻孰重、孰先孰后,进而追求纲举目张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。
这就好比下棋,要考虑整体布局,要关注各个方位,要推进各个区域和点之间的联系、支持与呼应,而不仅仅把目光盯在某一个区域、方位或者是具体的点上而不顾及其他。我们追求在全国,乃至更大的范围内发展鹤立教育,不能不考虑我们设置的每一个点,对现在和未来,对鹤立“一盘棋”的影响。从这个目的出发,大都市和省会城市的优势显然是南阳这样的城市无法比较的。
与战略相对应,当然还有战术。我在南阳运作的过程中,关注的多数还是战术问题,具体的招生方法、教学方法。不可否认,这些当然也很重要,它将决定某一场战役是否能赢,某一次交锋能否获胜,一个幼儿园能否生存、立足。但仅有战术是不够的,特别是想再上台阶,进一步拓展市场、扩大规模、为未来做长远设计时,就必须将战术纳入战略的指导之下、控制之下。由战略部署,决定我们下一仗在哪里打,怎样打,我们的兵力如何部署,这样才可能使我们的市场做大、做强。
有些朋友喜欢在战术的层面上徘徊,特别关注某一个具体问题,某一个具体措施,缺少战略意识。这样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会极大地抑制企业或团队的发展与超越。并且,这样的做法难以形成合力,容易出现各自为政、本位主义、地方割据的局面,而不利于整体和全局的迅速成长。
我想离开南阳,还有第四个原因,就是南阳的文化和经济不够发达。南阳虽然是一座历史名城,百里奚、张衡、张仲景、诸葛亮都与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,但那毕竟都是历史。而历史上的发达与先进,往往与现实的闭塞、落后相伴随。在这里,家长的教育观念还相当滞后,这一点我已深有体会。
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市场唤醒、市场培育的工作,但那需要漫长的时间,极大的精力,只能取得事倍功半的回报,而我追求的是事半功倍。我认为那些文化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比起南阳来就应该有更多的优势。
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:农村的孩子不需要教育吗?既然你是由于珍爱人的生命而推广这样的教育,那么农村和偏远地区、中小城市的孩子们生命不同样需要珍爱吗?的确如此!但一项事业要发展、要成长,是有其内在规律的。如果违背这种规律,就无法生存,更不能发展,那又如何实现其价值呢?这就好比,能够为穷人提供捐赠的往往是富人而不是穷人,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这个能力。鹤立教育只有在保证生存,并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,才有可能为更多的孩子,包括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积极的帮助。
我认为办学还是应该选择事半功倍的区域,这样才能提高发展的效率,迈开前进的步伐。如此看来,选择办学地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,就好像一粒种子,落到土壤肥沃、水源充足的地方,就有希望长得茁壮、长得繁茂;如果落到贫瘠的土壤上,存活都是个问题,哪还能长得好、长得快啊!
我要向外发展,但要去哪里落脚,那时还是比较模糊的。不过我有一个原则—到省会级的大城市。我首先想到的是沈阳,因为那里毕竟是我的故乡。当时我的东北人情结还比较重,觉得东北的家长重视教育,舍得投资,东北人办事麻利、爽快、有效率。但我也知道沈阳的场地难找,租金也一定很高。
我委托我的同学,也就是大江的妈妈,在沈阳帮我打听;同时我也在打别的地区的主意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,这也是我比较向往的城市。不过我非常缺乏这方面的人脉资源。
这时,我们幼儿园的周老师,给我带来了郑州的消息。说有个闲置两年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可以出租,每月租金三千元,一下子让我怦然心动。
那么资金问题怎么办呢?前边已经说了,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,现在每个月有两千元的收入,而这两千元连人家的房租都不够,何况还需要前期投资呢。这将如何是好!而且,新的区域的发展,必须有个前提,即现在的根据地能够正常运转,这样既不会牵制我太多的精力,还可以稳定地提供资金的支持。可是我一旦离开,管理工作、教学工作由谁来负责,这个矛盾就凸显出来了。
我那时坐镇桐树庄,有一个姓彭的老师给我做助手,她比较聪明,管理也有些办法,但从顾全大局和忠诚敬业方面来看,不如林海欣。
那么,此时林海欣在做什么呢?她主要负责永安村,保证那里的稳定和良性运转。此时的唐河和丝织厂后街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,永安村每月有一千来元的结余,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尽管有这么多问题,有这么多困难,不过我还是不死心,到郑州去发展的激情,时时在我心中鼓荡,因为我太渴望了,我渴望郑州的广阔空间,渴望它作为省会城市发展的高度,渴望它交通的便利与发达,也渴望那所建筑面积在1700多平方米的配套幼儿园。
到那时为止,我所办的幼儿园,还都停留在家庭小作坊的层面。私人宅院,有个三五百平方米已经不错了。我多么希望摆脱这种层次和规模,而进入规范的幼儿园运作轨道,那将是一个质的飞跃。这时,周老师再一次传来郑州的消息,说租金还可以商量。我决定亲自前往进行实地考察。

2015年8月,张鹤立女士在澳大利亚珀斯,为当地中文教育界人士介绍“鹤立教学法”与“鹤立教材”
下卷
十三、得陇望蜀
到1991年的9月,且不说是大是小,是好是坏, 我们在南阳已经有了四所幼儿园,在园的幼儿也达到四百多了。这里除了有前文述及的永安村幼儿园、唐河幼儿园、桐树庄幼儿园之外,还有后来创办的丝织厂后街幼儿园。
此时,唐河的幼儿园还是几十个孩子,只赔不赚;丝织厂后街幼儿园刚开办不久,也是只有投入没有回报;而桐树庄幼儿园则成为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,每个月大概能有二千元的利润,这对当时的我来讲,已经相当可观了。
尽管发展势头还好,幼儿园也基本进入良性运行的轨道,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南阳不是最佳选择,也不是我的久留之地。直觉告诉我:在南阳,难以大跨度地实现我的教育追求与梦想。
一是地方小、人口少,这就意味着市场有限、规模受阻、舞台太小,难以唱大“戏”。我那时有一种感觉:在南阳市的西边打一拳,就会把东边的人打倒,也就有这么大范围!就算在南阳各个区域,都发展起我们的幼儿园,从规模和数量上也难以达到我们的理想状态。
大家了解蛇和蚕吗?蛇和蚕长到一定程度,就要蜕皮。这时,它把身体从原来的壳中解脱出来。只有这样,它才能够继续长大;不然的话,那层已经板结的皮囊,就会抑制它的生长。虽然在蜕皮的过程中它显得很弱小很无助,甚至失去抵抗和防御的能力,成为天敌的美餐,但它必须这样做,否则它就没办法长大,没办法成熟,没办法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我意识到我也到了“蜕皮”的阶段。南阳的狭小,就好比是蛇和蚕的外皮,当我们“长”到今天的程度,已经感觉到了它的束缚和限制。只要我们想长大,就应该从这张“皮”中解脱出来。
不知为什么,鹤立教育总有一种“长大”的渴望,总是充满“长大”的激情。如果它一天不在品质和规模上有所提升和发展,就会觉得不大对头。一年多来,我们从一个孩子到几个孩子,从偏居西北的小门小户到市区有名有姓的幼儿园,从一所幼儿园再到现在的四所;一般的眼光来看,发展速度也算可以,可为什么还不满足,还不停下来舔舔伤口,梳梳羽毛,而要继续奔走,继续远航呢?没办法,我的体内一直鼓荡着“长大”的激情,充溢着发展的热望。这种激情和热望,虽然有时候让我盲目,让我失足,但我认为这是技术的问题,是思维方式的问题,而激情本身并没有错,它需要的是理性的控制和告诫,而不是消减和冰冻。
我相信,任何人的成长和发展,任何企业的成长和发展,包括一个团队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长和发展,其内在的动力都离不开这种激情和渴望。这是生命最本能的冲动,是生命上演的剧目之所以丰富多彩、波澜壮阔的最根本的原因。就好比整个生物世界从简单到复杂、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就离不开这种内驱力一样。
一个孩子最强烈的冲动就是长大,这是最本真的童心,而只有保留这种童心的人,才能不断地获得发展、求得进步。一个企业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若想发展、进步,又何尝不需要这种“长大”的冲动呢?我相信:如果什么时候失去了这种热望,那么未老先衰的征兆就会出现。
中国的企业和国外的企业相比较,从总体来看,其发展的速度、规模和层次是相距甚远的。我想,一个最重要的原因,就是我们普遍缺少这种“长大”的激情和渴望。我们奉行“小富即安”、“知足常乐”、“求安求稳”的信条;只关注物质生活,而缺少精神生活的需要,在“吃饭活着,活着吃饭”的层次上徘徊,而缺少社会责任感,缺少对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;所以够吃够花就行了,何况不仅够这一辈子吃喝,连下一辈都够了呢!
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,当一个人、一个企业、一个团队解决了生存问题,进入小康状态之后,发展之“火”就开始缺“氧”,也就失去了继续长大的冲动与激情,这应该是中国很多企业,包括幼儿园,出现“盆景效应”和“侏儒症”的原因吧。
我们为什么要长大?说到底这是生命应有的追求与冲动。你问蛇和蚕为什么要蜕皮?你问蝌蚪为什么变成青蛙?幼虫为什么变成蝴蝶?山上的树为什么从岩缝中倔强地生长并不断地指向蓝天,难道这需要理由吗?如果说理由的话,那就是这些生物体自身的使命。
鹤立教育要完成自己的使命!
谢天谢地,这种小农意识虽然不能说对我没有影响,但起码我还没有完全被它控制,这大概要感谢我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。从我父亲那里,我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种影响:作为人要活得有价值,要杰出、要创造、要有所作为,而不能虚度年华,愧对生命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化开始蜕变成了“侏儒文化”、“盆景文化”。而这种文化的典型特征,就是不许长大、不许卓越、不许杰出。而让你变得平庸得不能再平庸、渺小得不能再渺小,甚至让我们丢掉很多“人”的本质和特性,变成一头“猪”—一头只知道吃吃睡睡,摇头晃脑,至多再加上个传宗接代的“猪”,以防断了香火。
在我生活的青少年时代,接受的都是这种教育。为了摧残个性,毁灭创造,还发动了一系列破坏性极强的运动,什么反对“白专道路”,不许“成名成家”,甚至“读书无用”,做“白卷先生”,做四肢发达、大脑贫乏的劳动者。人们只能躺在物质生活的泥潭里打滚,而不能有精神生活、情感生活,不能有梦想,不能有境界和追求,更不能有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理解。
多么可怕!这不正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吗?这不正是我们文化中最黑暗、最不人道的一面吗?她让人不能作为人来活着,而只能作为物、作为畜牲来活着。
我有幸没有被这种文化彻底吞没。我怎么能不心怀感激、来响应生命对我的呼唤呢!所以,我必须长大,我要“蜕”去南阳这张“皮”,而给自己寻找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在南阳,存在着的第二个问题是交通不便。那时南阳没有主要铁路干线经过,距离郑州这个交通枢纽也比较遥远。当年乘坐汽车需要12个小时,而且路况很差。至于那时的车况就更糟了—破烂、狭窄,四处透风,哗啦啦地响;而车主为了多拉乘客,两排座位挤得人都喘不过气来,用来治“罗锅”正好。
汽车在这样的道路上行驶,不仅颠簸,而且还不安全。路两边的脏、乱、差也影响人的心情。如果不是万不得已,又有谁愿意品尝这样的滋味呢?
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鹤立教育难以向外传播,我们既不方便走出去,外边的人也不愿意走进来。而这不符合我的理想、我的意愿。
从我独立办学的那一天开始,我就盼望着能让鹤立教育走遍全国,走向世界。虽然当时还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和方式是什么,但我知道这一天肯定会到来。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向这一天逼近、靠拢,我下一步想采取的步骤也必须围绕这个目标。可是在南阳,这只能是遥远的梦想。
我在念大学的时候,学的是汉语言文学,但真正对我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是生物学和东方哲学。生物学让我体验到了生命的神奇与美妙、和谐与珍贵,连一只虫子,其生命都弥足珍贵,更何况我们人类!人类是宇宙的杰作,是上帝的珍品,是日精月华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形成的结晶。
作为个体,人的生命都来自于极端的偶然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战战兢兢地呵护她,不怀着虔敬的情感去打磨她。观照现实,我们会发现较长的一段时间里,生命在教育的视界里历来是缺席的。审视教育过程中对生命的浪费、作贱、扭曲的现象更是让人瞠目结舌,无法忍受。我在了解和感受生物发展的过程中,被塑造了,被提升了,使我产生了由此及彼的情感—从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角度,拓展到对其他生命,尤其是对年轻人的生命负责任的高度。我深知若实现这种愿望,我的脚步不能停留在南阳这个地域内。
说到这里,肯定有人说我狂妄、自负,但我可以坦然地告诉你: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,我就是将这项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使命。我感觉,有这种心态的人不是多了,而是少了,而我居然是这少数中的一位。对此,我感到骄傲,我感到自豪。
我认为南阳不理想,还有第三个理由:南阳属于中小城市,缺少号召力、影响力,不具有制高点上的战略价值,势必影响人们对鹤立教育的认可度以及积极追随的心态。
人们往往爱屋及乌,因为向往这座城市,便也不自觉地对这个城市的相关事物喜爱起来,靠自己的想象给它涂上金边、插上鲜花。相反,假如一座城市在人们的心目中评价不高,那么与它相关的事物,即使再好、再出色、再卓越,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也要打折扣。就像人出国旅游一样,到了国外即使东西再贵,再假冒伪劣,也要买上一大堆。回到家里才发现,家门口的商店里就有,比国外便宜得多,而且质量可靠、维修及时。但家门口的东西他偏偏不买,偏要到国外受骗,人有这种心理,你又如之奈何呢。
特别是我们中国市场开放时间不长,大家的市场经验还比较匮乏,缺少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能力。所以,就像小品《卖拐》中的范伟那样,容易被赵本山“忽悠”。人们愿意追星,愿意崇拜偶像,城市也有明星城市、偶像城市,而像北京、深圳、广州比起南阳来肯定要“明星”一些、“偶像”一些,甚至郑州比起南阳也不知道优越多少倍—尤其对河南境内的城市来讲。
因此,鹤立教育应该抢占战略制高点,这样才能对更广阔的空间形成辐射、产生影响。这既是在空间上的制高点,也是在人心理上的制高点,使大家乐于认同与追随,这便是我所说的战略意义。
前面谈到我对东方哲学的接触和热爱,我认同这种哲学思想中体现出的整体—联系和辩证—变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,而这也是我进行战略思考的哲学依据。
什么叫战略思考呢?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关注局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,相互制约,促成各要素之间的整合与互动。与此同时,再在关系中辨别孰轻孰重、孰先孰后,进而追求纲举目张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。
这就好比下棋,要考虑整体布局,要关注各个方位,要推进各个区域和点之间的联系、支持与呼应,而不仅仅把目光盯在某一个区域、方位或者是具体的点上而不顾及其他。我们追求在全国,乃至更大的范围内发展鹤立教育,不能不考虑我们设置的每一个点,对现在和未来,对鹤立“一盘棋”的影响。从这个目的出发,大都市和省会城市的优势显然是南阳这样的城市无法比较的。
与战略相对应,当然还有战术。我在南阳运作的过程中,关注的多数还是战术问题,具体的招生方法、教学方法。不可否认,这些当然也很重要,它将决定某一场战役是否能赢,某一次交锋能否获胜,一个幼儿园能否生存、立足。但仅有战术是不够的,特别是想再上台阶,进一步拓展市场、扩大规模、为未来做长远设计时,就必须将战术纳入战略的指导之下、控制之下。由战略部署,决定我们下一仗在哪里打,怎样打,我们的兵力如何部署,这样才可能使我们的市场做大、做强。
有些朋友喜欢在战术的层面上徘徊,特别关注某一个具体问题,某一个具体措施,缺少战略意识。这样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会极大地抑制企业或团队的发展与超越。并且,这样的做法难以形成合力,容易出现各自为政、本位主义、地方割据的局面,而不利于整体和全局的迅速成长。
我想离开南阳,还有第四个原因,就是南阳的文化和经济不够发达。南阳虽然是一座历史名城,百里奚、张衡、张仲景、诸葛亮都与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,但那毕竟都是历史。而历史上的发达与先进,往往与现实的闭塞、落后相伴随。在这里,家长的教育观念还相当滞后,这一点我已深有体会。
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市场唤醒、市场培育的工作,但那需要漫长的时间,极大的精力,只能取得事倍功半的回报,而我追求的是事半功倍。我认为那些文化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比起南阳来就应该有更多的优势。
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:农村的孩子不需要教育吗?既然你是由于珍爱人的生命而推广这样的教育,那么农村和偏远地区、中小城市的孩子们生命不同样需要珍爱吗?的确如此!但一项事业要发展、要成长,是有其内在规律的。如果违背这种规律,就无法生存,更不能发展,那又如何实现其价值呢?这就好比,能够为穷人提供捐赠的往往是富人而不是穷人,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这个能力。鹤立教育只有在保证生存,并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,才有可能为更多的孩子,包括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积极的帮助。
我认为办学还是应该选择事半功倍的区域,这样才能提高发展的效率,迈开前进的步伐。如此看来,选择办学地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,就好像一粒种子,落到土壤肥沃、水源充足的地方,就有希望长得茁壮、长得繁茂;如果落到贫瘠的土壤上,存活都是个问题,哪还能长得好、长得快啊!
我要向外发展,但要去哪里落脚,那时还是比较模糊的。不过我有一个原则—到省会级的大城市。我首先想到的是沈阳,因为那里毕竟是我的故乡。当时我的东北人情结还比较重,觉得东北的家长重视教育,舍得投资,东北人办事麻利、爽快、有效率。但我也知道沈阳的场地难找,租金也一定很高。
我委托我的同学,也就是大江的妈妈,在沈阳帮我打听;同时我也在打别的地区的主意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,这也是我比较向往的城市。不过我非常缺乏这方面的人脉资源。
这时,我们幼儿园的周老师,给我带来了郑州的消息。说有个闲置两年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可以出租,每月租金三千元,一下子让我怦然心动。
那么资金问题怎么办呢?前边已经说了,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,现在每个月有两千元的收入,而这两千元连人家的房租都不够,何况还需要前期投资呢。这将如何是好!而且,新的区域的发展,必须有个前提,即现在的根据地能够正常运转,这样既不会牵制我太多的精力,还可以稳定地提供资金的支持。可是我一旦离开,管理工作、教学工作由谁来负责,这个矛盾就凸显出来了。
我那时坐镇桐树庄,有一个姓彭的老师给我做助手,她比较聪明,管理也有些办法,但从顾全大局和忠诚敬业方面来看,不如林海欣。
那么,此时林海欣在做什么呢?她主要负责永安村,保证那里的稳定和良性运转。此时的唐河和丝织厂后街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,永安村每月有一千来元的结余,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尽管有这么多问题,有这么多困难,不过我还是不死心,到郑州去发展的激情,时时在我心中鼓荡,因为我太渴望了,我渴望郑州的广阔空间,渴望它作为省会城市发展的高度,渴望它交通的便利与发达,也渴望那所建筑面积在1700多平方米的配套幼儿园。
到那时为止,我所办的幼儿园,还都停留在家庭小作坊的层面。私人宅院,有个三五百平方米已经不错了。我多么希望摆脱这种层次和规模,而进入规范的幼儿园运作轨道,那将是一个质的飞跃。这时,周老师再一次传来郑州的消息,说租金还可以商量。我决定亲自前往进行实地考察。
【凤凰华人资讯网报道】
分享到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