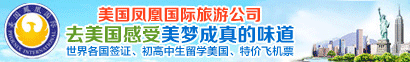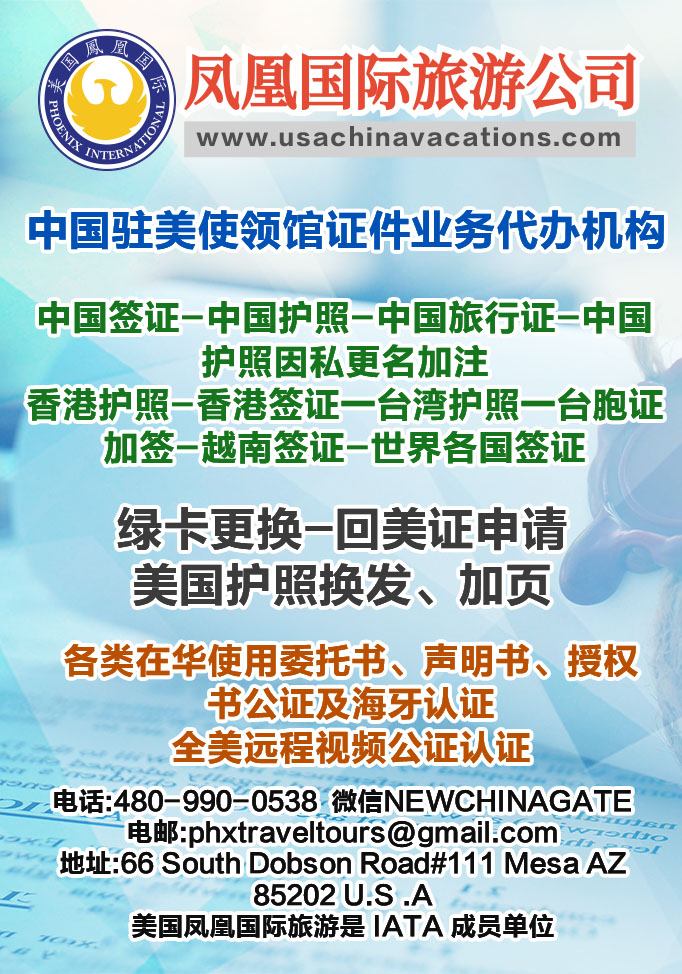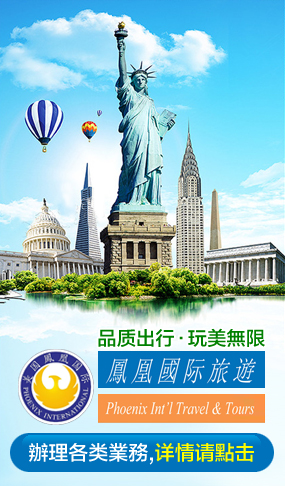凤凰华人资讯网|杨文田 特评

2025年6月27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的一番话,再次震动了整个政坛与媒体圈。他在谈及接连不断的暗杀威胁时感慨:“如果早知道这么危险,我可能不会参选。”这一句话,在外人看来或许只是一种临时情绪表达,但若深入剖析,却极具讽刺意味,也暴露了这位总统在第二次任期中的自我认知、政治焦虑与危险治理。
特朗普口中所谓“危险的总统”,并非空穴来风。美国历任总统中,已有四人死于暗杀,多人遭遇未遂袭击,这一数字在全球政体中颇为罕见。然而,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总统“职业危险性”这一表象,而在于特朗普本人是否也在制造这种“危险的政局”?他是否只是一个权力的“受害者”,还是一个把政治引向极端与分裂的“制造者”?当特朗普自己哀叹“如果早知道”时,整个美国其实正在经历一场制度性信任的崩塌。
我们不得不回到2023年宾夕法尼亚州的那个竞选集会。那是特朗普近距离遭遇枪击的惊魂一刻,子弹擦过他的右耳,留下伤口与“悸动”。从那时起,他更频繁地提及“安全问题”,并将其政治化、媒体化,甚至变成了自己政治斗争的筹码。如今,他甚至将担任总统与“斗牛士”“赛车手”这些高死亡职业相提并论,称“总统的死亡率约为5%”。这是一种夸张的政治语言,也是一种刻意的牺牲者叙事,特朗普在塑造“危险中的英雄”人设的同时,也在进一步强化他对国家安全、司法体系与媒体环境的强烈不信任。
然而,真正危险的,可能不是总统职位本身,而是特朗普治下的政治生态。
根据《华盛顿邮报》与多家美国智库的统计,美国已进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暴力时期。自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事件以来,已有超过300起政治暴力事件记录在案。其中多数都与右翼极端主义、阴谋论推动者以及仇恨团体密切相关。特朗普并未有效地遏止这些力量,反而时常以“人民的愤怒”“自由的呐喊”之类话语为其合理化、浪漫化,甚至美化。
从表面上看,特朗普似乎是“被威胁”的一方,然而,问题的根本恰在于他自己长期将政治煽动作为手段、将对手妖魔化为策略,使美国社会内部裂痕不断扩大。政敌不再是辩论中的对手,而是“邪恶的敌人”;媒体不再是监督的力量,而是“人民公敌”;司法机关不再是宪法的守门人,而是“猎巫集团”。这一系列话术下,特朗普并非只是安全风险的“接受者”,而更像是一个政治极化的“加速器”。
回顾美国历史,总统职位确实不乏危险时刻,林肯、加菲尔德、麦金莱、肯尼迪相继遇刺,里根险些丧命。但他们所面对的威胁,多源于孤立的极端分子、精神障碍者,或冷战结构下的意识形态仇恨。而如今的美国,总统面对的威胁已演变为结构性暴力:阴谋论媒体、极端主义社交圈、枪支泛滥、以及“合法暴力”的舆论支持。更讽刺的是,这些危险,正是特朗普“再造美国”过程中催生出来的副产品。
这不禁让人反思,特朗普所谓的“后悔参选”是否只是权力话术中的一环?从“美国优先”到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,从移民禁令到媒体封杀,从退出气候协定到制造贸易战,特朗普的政治路线早已激化全球与国内多重矛盾。如今的美国社会,不仅是政治暴力的受害者,更是制度信任危机的泥潭,总统与民众互不信任,红蓝州彼此敌对,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合作基础。
在这种氛围下,任何总统上台都可能面临高风险,但特朗普的风格,自恋、极端、好斗、仇视批评,使得这种风险被放大。也就是说,他不是“受害于危险”,而是“危险的放大器”。
此外,他的这番“后悔参选”言论,也值得从另一个层面解读:这是逃避责任的前奏吗?
从特朗普第二次任期开始,他几乎将所有问题归咎于“前任政府”“深层政府”“司法体系”“假新闻媒体”,而今又将担任总统的危险性推给“没人告诉我有多危险”。这不免令人怀疑:一个渴望连任、又意图掌控一切的领导者,在真正面临政治现实与生命威胁时,是不是也会借“危险”之名,合理化未来某种退出、拒绝竞选或放弃法律责任的路径?
不可否认,特朗普的支持者基础仍十分坚实,他可以靠一次集会、一场直播动员起百万粉丝。但在一个社会撕裂、舆论极端的时代,他是否也该反思:危险的不是总统身份,而是政治的方式?
倘若特朗普真如他说所言,后悔参选,那么更应后悔的,不该是这个位置的危险性,而是他本人对这个国家带来的撕裂与焦虑。
政治不是角斗场,更不是真人秀。总统是人民意志的承载者,不是煽动者,也不是自怜者。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,应该用言行重建信任,而非用危险叙事加深恐惧。
特朗普可以说出“如果早知道就不参选”,但美国人民更应该问的是:“如果早知道他是这样的总统,我们是否会让他上台?”
这是今天美国所面对的最沉重问题。而答案,必须由制度、媒体、教育与理性共同给出。否则,危险不仅属于总统,也属于这个国家的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