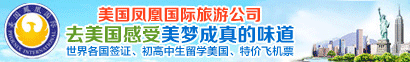作者:郑少逵
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标本式农民,有生以来,从未离开过田地。他如今已年过六十,在观念中,他已步入晚年的门槛,实实在在是个老头子了。他还在耕种着他的一块田地,百来棵荔枝,一园自给菜——全家吃不完时,还能卖点作旱烟钱。但听老母亲说,有时老父亲触景生情,偶尔会有深深的感叹:“老了,不知不觉中老了。就是活到八十多,又有几个年头?!”
是的,出身贫苦、厚道、耿直、坚韧却又不乏保守色彩的老父亲,为着我们一家,一直以来咬着牙默默苦干着,恍惚间,已经是个老年人了!如今,虽然我们子女都已独立生活了,可这于他又有多少的慰藉呢?
这几年,随着祖父祖母相隔一年多的逝去,父亲在家庭中的老辈身份凸显了出来;加上六十甲子这道坎,他的心境不自觉掠上一丝丝荒凉、凄清。
田玉田火烙画:父亲
而就在这时候,我在距老家不远的小城里有了一处住所,我需携小家离开父母亲单住。这更在他的心境蒙上一阵霜雾。父亲一方面为儿子能独立而欣喜,一方面又因家庭境况的变化而心悸。他想到我一小家的离开使他俩老会更加孤寂;他怕增加我们的负担而不跟着出来;他怕过不惯小城的笼居生活,更离不开润透着他血汗的田地;他也心系着我的那未成家立业的弟弟。在我临近搬家的那几天里,父亲明显的吃睡不香、烦燥闷气。直到我努力安慰了他一番,他才把愁容收起。
老父亲的身体虽算硬朗,但毕竟瘦小,加之年纪到了,体力明显的退化。对一些重活,他已自感不支。他力所能及,就勤恳地耕作他的园地。对于那一垄田,他就让出了一季给年轻的亲人种,因为他只种一季就足够我们全家一年的口粮了;对于荔枝园,也管得较少;对于村旁离家很近的那一块菜园,他却一直不辍劳作。为了尽量使家人能不间断地吃上自家菜园上的菜,他把菜园分成好几小块的,不同季候间种了不同的青菜或瓜豆。每天早早晚晚,他都一头钻进他的园地里。
搬家以来,我一小家还在继续吃着父亲种的粮食,也不少吃着父亲种的瓜菜。
有一次,我企图减少父亲劳作的负担,在粮店买了米。父亲看我一段时间没回去带米,估算我带出来的米应吃完了,便打电话问我怎么那么久没回去带米。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,嗫嚅着说:“吃完了没时间回去带,顺便在这外面买了一包……也怕家里的以后不够吃。”父亲生气了,他说:“怎么不够?吃得完吗?外面买的比自家的更香吗?你没时间,打电话回来,我托人捎去或自己带去都行!”不久后的一个晚上,他居然用单车亲自为我带了一大袋米来!看着他单薄的身躯,想着他劳作的疲苦,我内心无限滋味翻涌。以后,在老家的父母亲更留意我一小家的口粮了,他们总是及时地提醒我回去带米——他们可能也意识到我主动回去要米有点难以为情。
每次我带小孩回去走走,父亲总要张罗着到菜园摘一些让我们带出来。我们不敢冷却父亲的盛意了,有时还主动去菜园摘菜。我们看得出父亲在他的劳动成果受我们欢迎时的喜悦。他尽挑好的让我们多带些出来,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:“自己种的菜就图个自家人爱吃!”
有朋友戏言我:“老父亲种的米菜好吃吗?你还好意思吃吗?”
是啊,是啊,内中滋味我何尝不知?酸甜苦辣,那都是老父亲血汗的结晶!同时,我也吮吸着老父亲坚韧精神的液汁,叫我时刻懈怠不得、矫情不得。不能让老父亲休田安闲,每每令我内疚不安;在惶惑之时,我只愿老父亲能种少点轻松点,心态上能随遇遂意。有时我也迟疑起来:过惯了田园生活的老父亲,一旦离开田地,能以什么自得其乐呢?苦巴巴劳作了大半辈子,就希望能过上好日子;没想到竟可能会将就沉浸一生!我曾以一句“在生活与 工作中获得真正的伟大感才是人生的真谛”的哲语自慰,但随着岁月的无情流逝,看着老父亲的头发日益灰白却依然劳累的身影,我不免也感叹着类似老父亲的感叹:“人生如许?”
赞